母亲离开我已经33年。但在我心中,母亲并没有走远,她只是在某个地方等着我。从来不需要想起,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明天是母亲节。读过许多怀念母亲的文章,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著名作家史铁生、贾平凹、肖云儒的三篇文章。今天,我读给您听,共同祝福天下母亲幸福安康。
——白燕升
秋天的怀念
史铁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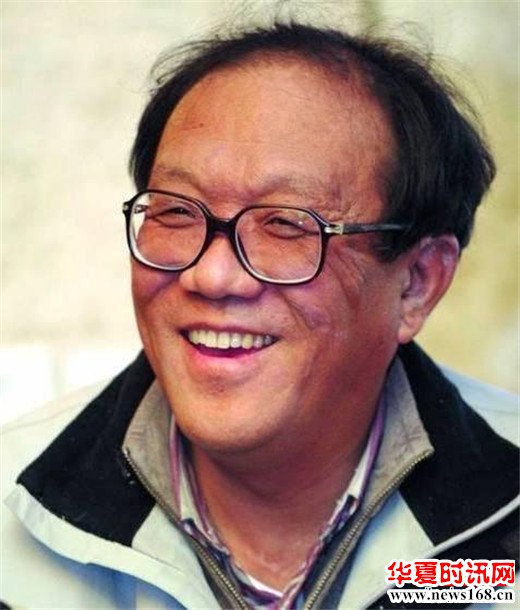
双腿瘫痪后,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。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,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;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,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。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,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。当一切恢复沉寂,她又悄悄地进来,眼边红红的,看着我。“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,我推着你去走走。”她总是这么说。母亲喜欢花,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,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。“不,我不去!”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,喊着,“我可活个什么劲儿!”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,忍住哭声说:“咱娘儿俩在一块儿,好好儿活,好好儿活……”
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,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。后来妹妹告诉我,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。
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,看着窗外的树叶“唰唰啦啦”地飘落。母亲进来了,挡在窗前:“北海的菊花开了,我推着你去看看吧。”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。“什么时候?”“你要是愿意,就明天?”她说。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。“好吧,就明天。”我说。她高兴得一会坐下,一会站起:“那就赶紧准备准备。”“哎呀,烦不烦?几步路,有什么好准备的!”她也笑了,坐在我身边,絮絮叨叨地说着:“看完菊花,咱们就去‘仿膳’,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。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?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,跑着,一脚踩扁一个……”她忽然不说了。对于“跑”和“踩”一类的字眼,她比我还敏感。她又悄悄地出去了。
她出去了,就再也没回来。
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,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。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。看着三轮车远去,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。
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,她正艰难地呼吸着,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。别人告诉我,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……”
又是秋天,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。黄色的花淡雅,白色的花高洁,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,泼泼洒洒,秋风中正开得烂漫。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。妹妹也懂。我俩在一块儿,要好好儿活……
写给母亲
贾平凹

人活着的时候,只是事情多,不计较白天和黑夜,人一旦死了,日子就堆起来;算一算,再有二十天,我妈就三周年了。
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,总要说一句:这是谁想我呀?我妈爱说笑,就接茬说:谁想哩,妈想哩!这三年里,我的喷嚏尤其多,往往错过吃饭时间,熬夜太久,就要打喷嚏,喷嚏一打,我便想到我妈了,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着我。我常在写作时,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,叫得很真切,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来。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,我一伏案写作,她就不再走动,也不出声,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,看的时间久了,她要叫我一声,然后说: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,出去转转么。现在,每听到我妈叫我,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,心想我妈从棣花来西安了?当然房间里什么也没有,却要立上半天,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,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,或许,她在逗我,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,我便给她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,要说上一句:我不累。
我妈是一个普通的妇女,缠过脚,没有文化,户籍还在乡下,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。已经很长时间了,虽然不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,可我出远门,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,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,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。
在西安的家里,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,我没有动一件家具,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,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。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给自己说,我妈没有死,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。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,每晚湿热得醒来,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。待清醒过来,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,应该是清凉的吧。
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,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,我准备着香烛花果,回一趟棣花了。但一回棣花,就要去坟上,现实告诉我妈是死了,我在地上,她在地下,阴阳两隔,母子再也难以相见,顿时热泪肆流,长声哭泣。
母亲
肖云儒

我在编《民族文化结构论》这本集子的时候,常常想起我的母亲,要是她还活着,今年已是80岁整。二十八年前弃我而去,她52岁,正好是我现在的年纪。
几十年来,思念有如流不断的河水,剪不断的云翳。思念的频率,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。
而在研究学问时,如此执拗地、排解不开地想起她,还是头一次。
好不惑然。
半岁丧父,亦无兄弟姐妹,母亲终生守寡,将我拉扯大。我于她,她于我,都是唯一的、独有的。她携着我,我搀着她,脚印交织在人生路上。
母亲大半生任教于中学,晚年调入图书馆,一直住在单位的单身房间。我初中以前,被寄放在外婆身边,她每周回来看我。高中起我在市郊一所学校住宿,每周必定回去看她。
有次她对我说:下星期有事不能回来了,不要想她。那分外的温存,使我过敏地感到这是要扔下我远行,竟然怀着少年人不该有的悲哀和惶惑,悄悄跟在母亲后面足有一个钟点,直到看见她确实进了学校的大门,而不是去了车站,才脚踏实地踅回。
又有一个星期天,因为下雨我留在学校没回家。雨停,已是过午,想不到她让一位学生步行15华里来看我。我便又步行15华里回去,让她确证儿子的安然无恙。那时中学生很少有自行车,我们用脚板一步一步丈量感情。
每一次离别,无论短长,母子都要和孑然一身的孤独作一次搏斗。大约从那个时候起,中国古典文学中描绘“倚门倚闾”的诗文书画,便一遍一遍地感动着我。
实在也苦了她。因着浓冽的爱不能不压抑自己的爱。
母亲是知识女性。整整四大本相册,记录着她挥斥方遒的激情的青年时代。
“一二·九”运动在北京的有轨电车上散发传单。
搂着卢沟桥的石狮子大笑。六位女同学平卧雪地,摆成六角的冰花。
在教会学校和美国神父对面论辩……
她并不封建,在自己的历史论文和历史剧中,一再为被封建文化窒息的中国女性呼吁。但在28岁守寡之后却没有重新组织家庭,尽管有人撮合,尽管外婆催促。我想那是为了我。成年之后,我才加倍痛彻地感受到母亲这样子生活的孤寂。孤灯冷月下的24年,八千七百多个日日夜夜,是容易的么?每当她听唱片,便有如一颗孤寂的心在自言自语。囿于当时的文化氛围,加之我不是女儿,上大学后几番欲言而未启齿。
母亲的感情生活中为儿子的自戕,使我终生内疚。
母子之间的爱都无私。
就连母爱,她也不能不斟酌着、节制地表露。
作为寡母,她必须同时具有父之尊、师之严、友之诤。
对我的功课近乎残酷的督查,每每使外婆暗自流泪。至今想来,仍然引起甜蜜的战栗。我甚至恨过她,又终于懂得能够从小接受大松博文式的教练,是我的造化。那远低于家庭经济水平的简朴要求使我简朴,那不完成计划不能睡觉的训令使我勤奋。铁器是在铁砧上锻打出来的,若要一位寡母如此来锤打自己的独子心里是怎样的滋味?
直到今天,母亲严厉的目光,仍在天宇中监测着我,催我奋力奋进,催我自思自审。
由不惑而届知命,母亲有了一点变化。先是稍稍超脱了繁忙的学校行政,而后又稍稍超脱了省图书馆的机关事务,重新拣起历史专业,开始了女性系列历史剧的写作:《嫘祖》《班昭》、《李清照》、《赵飞燕》《武则天》……直到《秋瑾》。有的演出了,更多的存于箧底。《秋瑾》只写了第一场,便和一封给我而未发出的信,一块掰开吃了一半的点心,永远留在了桌上。——第二天,她被死神遽然劫持,因为脑溢血在省人代会发言后倒下。从此长卧于江南的红土地中。
转向历史,对母亲来说,也许是一种人生的沉凝,也许是一种感情的蒸腾,我不得而知。却能感到,阅历总要使人皈依土地,皈依文化土壤。
也恰恰是由不惑而届知命,我的兴趣悄悄地发生转移,开始钟情于历史文化。内中原因也不得而知。分明不是神使鬼差,也不能说是接续母亲在52岁时戛然中断的工作,只能说是生命自然运行的结果了。
生命来源于母体。精神根植于历史和现实既在文明成果。每个人都从脚下的土地上起步,经历了青春的翱翔,总有一天要重新降落在土地上。尽管那是另一块土地,尽管那里有另一番风致。
自从剪断脐带,我和母亲的联系由血肉的直接交溶转而为语言和文字的传递,为眼的流盼,为心的感应。50多年中,我们日甚一日娴熟地在各种有声和无声的频道中联系,哪怕地隔千里,哪怕分隔于两个世界,一直相依为命。
有时我想,母亲之于我,已经是一种传统,一种标尺,一种基座,一种象征。有了喜悦,走了弯路,面临选择,很自然地就和冥冥中的她对话。那往往是以历史和人生的基座在检视自己。
真应了郭沫若早年的名句:“一的一切,一切的一”。母与子这两个“一”,占有着对方的“一切”。母与子这两个“一切”,凝结为对方的“一”。
近30年了,回江南扫墓的机会那么少,我几乎没有正式祭奠过她,也没有一篇怀念母亲的文字。这都是儿子的罪过。
我的母亲,愿这本涉及历史和文化土壤的书,能寄给你些许的慰藉,能赎回我如山的歉疚。(1992年1月28日12时,岚楼)








